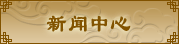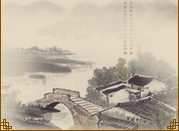文物再利用──澳门经验
随着澳门社会及经济的急速现代化,人口增长、土地紧缺及城市功能需求增加等问题日益突出,而这些问题都为澳门的文物保护方式及路向提出了挑战。针对澳门上述的现实状况,对文物实行保护性再利用是一项必要且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课题,文物保护应结合城市发展的进程,使得文物在消耗社会资源而得到保护之余,同时也应贴近社会生活并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及资源,发挥功能效益,回馈社会,从而实现文物的可持续保护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澳门文物保护现行法律规定
澳门于1976年8月7日颁布了第34/76/M号法令,这是第一条比较全面的文物保护法令,当中确定了澳门的文物清单及设立了“维护澳门都市、风景及文化财产委员会”,但该法令中基本没有关于文化遗产再利用的控制条文;1984年6月30日,第56/84/M号法令公布,该法令取消了原有的第34/76/M号法令,设立了“保护建筑、景色及文化财产委员会”,把澳门文物的分类修订为“纪念物”、“建筑群”和“地点”,更新了文物清单,同时对每一类文物的保护方法及利用作出了规定;1992年12月31日,第83/92/M号法令公布,该法令对第56/84/M号法令作出了补充修订,增加了一项“具建筑艺术价值之建筑物”的文物分类。目前,澳门的文物保护工作主要是根据第56/84/M号和第83/92/M号法令来执行,而当中四类文物的保护和利用规定主要如下:
纪念物:在未获得行政长官核准之前,不得全部或局部将之摧毁或进行更改、扩建、加固或修葺的任何工程;而且,纪念物的再利用亦应于事前取得文化局的意见。
具建筑艺术价值之建筑物:只要不损害其原有特征,尤其是立面特征,并获得文化局的赞同意见后,则可进行扩建、加固、改建、重建、复原工程或对建筑物内部进行重整。
建筑群:其全部或局部之任何工程的进行需先取得文化局的赞同意见。
地点:在获得文化局的赞同意见后,可进行新楼宇或设施的兴建、或对现有的不动产全部或局部予以重建、改建、扩建、加固、修葺或拆卸。
从上述法令的相关条例中可以看到,澳门早于1984年就已开始对文物的再利用进行探索,努力寻求文物保护与文物再利用的平衡关系。
文物再利用的缘起
目前,澳门的法定文物共128项,当中“纪念物”52项,主要为教堂、寺庙和炮台;“具建筑艺术价值之建筑物”44项,主要为昔日较具特色的公共建筑及宅邸;“建筑群”11项,主要为民居;“地点”21项,主要为山体、公园和广场;所有文物共涉及417座建筑物,而当中除了少部分的文物是澳门公共财产外,其他的大部分文物均属于私人产业。
在澳门,单纯把文物作冻结式的保护方式并不现实。首先,不是所有的文物都需要采用冻结式的保护方式,只有内外价值都特别突出、且保留完好的文物才应如此;第二,冻结式的保护方式会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尤其对于土地资源紧缺的澳门来说更是难以负担,此外,因大部分的文物属于私人产业,冻结式的保护方式会涉及大量的业权人利益赔偿问题,难以符合社会及经济的发展需求;第三,冻结式的保护方式容易造成文物难以被接触、使用,从而使文物脱离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并由此导致文物逐渐失去活力并最终成为社会负担。针对澳门的现实状况,对文物实行保护性再利用是必要且具有实际意义的。
文物再利用的原则
文物再利用的原则是保护价值,适当利用,面向公众,融入生活。
首先,文物再利用的根本原则是必须以保护文物为大前提,充分保证在再利用的过程中不会损害文物的核心价值,能依然保存文物的固有个性,使得保护与利用两者能相兼容而不存在对立。
第二,文物的再利用应体现当代意义。虽然任何的再利用都必须建基于对文物的保护之上,但是,保护并不意味着把文物凝固为一个历史的瞬间,文物不应脱离时代及空间的发展而被一成不变地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完全忽略各时代所该留下的痕迹。文物是社会的组成,在社会发展的同时,文物亦应同步前进,不断满足当代社会的功能需要,在反映历史文化价值之余同时注入新的当代意义,不断丰富文物的功能价值及内涵。
第三,文物再利用须保证文物能被善用,确保能把文物用对以及用好。把文物用对指的是要为文物注入合适的功能,既能适应文物的物质环境制约,同时又符合文物的个性特质,不对文物的价值造成损害;把文物用好则是指注入的新功能应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文物是该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而且,文物是属于全社会的,需为公众共享,其使用应以向公众开放为目标,致力使文物融入社会生活。
文物再利用的模式
澳门文物再利用的方式可分为两大类:功能置换、焕发新生和注入新机、额外增值。功能置换、焕发新生是为原本功能已荒废的文物置入新功能,让文物焕发新生。如澳门博物馆和圣地亚哥酒店是利用昔日的军事炮台经活化利用而成、何东图书馆的前身则是一座建于1894年之前的葡式住宅、中央图书馆和历史档案馆的前身是建于二十世纪初的带新古典主义的住宅建筑群、而演艺学院音乐学校的前身是约建于二十世纪初的联排住宅、金融管理局办公大楼的前身是约建于1916年的私人住宅、塔石广场的前身是建于二十世纪初的学校操场。
在为文物注入新功能时,文物原有格局是否需要保留是首要考虑因素,随后就需要考虑新功能对空间的要求能否与原格局或空间重整后的新格局相适应。除了考虑新功能对物质空间的适应性,在实行功能置换时还要考虑新功能与文物的个性和氛围能否协调。合适的功能可使文物在重获新生时仍然保持原来的特质,但不合适的功能则会破坏文物的价值。
注入新机、额外增值是对需要维持原功能的文物注入额外的合适功能,进一步增加文物价值。在澳门,例如卢家大屋、大三巴等都是在文物中增加合适的额外功能而使文物增值的案例。当中,卢家大屋和郑家大屋都是典型的中式大宅,在修复后均保留了原来大宅的面貌以向公众展示,为求文物能与社会生活建立良好的关系,让文物成为大众生活的日常组成,在卢家大屋和郑家大屋当中额外增加了合适的新功能,卢家大屋会定期邀请国内的传统工艺艺人驻场表演并举办亲子工作坊,同时还会定期举办澳门艺术节的演出,不断推陈出新,丰富城市的文化生活;至于大三巴,除了作为遗址被保存外,还会作为艺术演出的场所,如举办音乐会、视觉艺术表演、巡游演出等。
当为文物额外注入新功能时,新功能与文物个性的相互协调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为文物注入额外功能的目的是要让文物进一步增值,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切不能本末倒置,因随意增加文物的功能而导致文物的价值受损。
文物再利用的行动策略
文物再利用的行动策略是官民携手、多方共赢。澳门文物众多,而且大多数文物皆为私人财产,故不可能单靠政府的力量就能实现文物的保护再利用,必须通过政府与民间的多方合作才能实现。对于属公共财产的文物,其再利用的实现相对简单,主要由政府主导,衡量社会诉求即可;但对属于私人财产的文物,其再利用的实现就会有着很多的困难,涉及到业主是否愿意开放文物、开放的功能是否能同时符合社会及业主的诉求等问题。在文物再利用的实现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平衡是关键因素,业主需要在文物再利用的过程中获得经济利益,公众需要获得享用文物的权益,而文物自身则需要得到保护的保障。
在澳门,德成按、何族崇义堂、疯堂十号创意园等都是成功体现官民携手推动文物再利用的成功案例。当中,德成按原是一座典型的当铺建筑,属于私人物业,自1993年结业后,物业一直空置,及至2000年,业主有意将其出售并实行改建,其后澳门政府主动与业主接洽,并协议政府出资140万元进行修缮,而修缮后,政府可利用当楼的底层以及货楼作为典当业展示馆,而当楼的其他楼层及相邻的富衡银号,则交回业主使用,其后该部分开设了集精品店、图书馆、茶馆及展览馆于一体的文化会馆;典当业展示馆及文化会馆均于2003年3月21日正式对社会开放。
上述案例的保护再利用,是政府与民间多方合作的成果,政府为文物的保护与修复提供技术及经济支持,从而换取对文物一定年限的使用权,甚或向业主进行租借,促使文物对公众开放,创建社会效益,并使文物的保护得到保障,而业主则于过程中得到了经济收益,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文物再利用的制约
在文物再利用的过程中,文物的物质空间以及文物的性格特质等非物质因素均会为再利用的新功能带来制约,不是所有的新功能都适合被置入文物当中。
首先,在物质空间上,文物的空间尺度以及空间布局均会为新功能和新使用者的行为模式带来限制。此外,文物的性格特质也会为新功能带来限制,对文物性格造成负面影响的功能都不应被置入,例如,在一座教堂中置入博彩功能就难以被接受。
新功能的注入是会对文物保护造成影响的,因为新功能总会对承载着文物价值的硬件载体提出改造要求,只要稍有不慎,文物的价值将会受到不可逆的破坏,得不偿失。
文物再利用的成功与否关系着文物保护能否得到有效的延续,文物再利用的手段及技术层出不穷,但目的必须要明确:一、文物的价值必须得到绝对的尊重;二、文物必须体现当代意义,面向公众,当好教育宣传,服务社会,不断增值;三、在保护中实现文物的再利用,在利用中实现文物的保护,文物保护与文物利用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只要处理得当,两者是可以并存的,相辅相成,使得文物在得到自身的保护之余创造出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